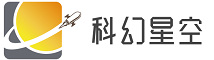我第一次见到我这位朋友是在敦煌。那时我独身一人前往中国,深入内陆的戈壁和荒漠中,参观那些历史悠久的壁画与塑像,当作是满足我个人爱好的一次身体与灵魂的双重探险。那时我撞见他正踩在石壁旁搭建的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用墨刷和纸张拓写壁画。
这不得不说是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莫高窟是中国政府作为最有价值的那一类国有文化财产所保护起来的,虽然有限制地开放给了外来游客,但是隔离我们与那些观摩对象的栏杆距离那墙壁看上去足有几英尺远。而他当时就在那栏杆里面,与那些宝贵的古老遗产亲密接触着,而看守人员和导游们对此熟视无睹。他显然不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绝对不是中国人。
似乎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他回过头来看了看我这边,表现出似乎有些惊讶的样子,然后又“工作”了不一会儿,便从脚手架上笨拙地跳下,向我走过来。
“很高兴见到你。你看起来是个内行。”
我感到有些惊讶,愣了一会儿之后摆了摆手。虽然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是我对于莫高窟,佛教或是中国文化都没有特别的了解。那离我的研究课题相距有些遥远。
“好吧…你在工作吗?别让我打扰到你。”我看了看他身后的墙壁。一副线条奇异地旋转着的黑白舞蹈人像浮现在贴在墙面上的大张白纸上。
“噢,别在意。这只是我的爱好。这些画面里也许藏着我想要的东西。你呢?”
“我?呃…,我只是个游客。”
“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他说。
“…好吧,我算是个考古学家。不过我的兴趣是美洲的古代文明——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听说过吗?”
“噢,那没关系。我也对美洲感兴趣,特别是奥尔梅克遗迹。”
“你知道奥尔梅克?”
他点点头,似乎想对我说什么,却突然挥手向我身后示意。几个看起来像是工作人员的中国人打开围栏上的大门,把里面的脚手架和墙上的拓本都带了出来。
从栏杆那边出来,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我犹豫了一下,握了上去。
“对了,”我四下看了看,似乎并没有人注意这边。“你为什么可以——”我指了指栏杆里面,压低了声音。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回答道。
我在随后的谈话中对这位朋友有钱的程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惊讶得知他在我任职的圣保罗大学资助建立了一座博物馆;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相谈甚欢,并且在那以后,不论是我们各自回到下榻的旅馆,还是直到我回到学校以后,也一直通过电子邮件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逐渐地,我发现这位古怪又吸引人的朋友是个矛盾的集合体:他对于现代科学和技术非常了解,却又是个十足的神秘主义者;他似乎十分富有,而且同各行各业都有着密切关系,能够充分调用我所能想到的,和有时候甚至都想不到的各种手段探索和收集那些他所感兴趣的东西,不过却从不向我透露自己除了这一爱好以外的任何背景。他自称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那些他所谓的“失落的智慧”;作为一个考古学家,虽然我还不至于像这位狂信者一样相信几千乃至几万年前存在着比现在更先进的古代文明,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与他兴味相投的交往。
有一次,我同他谈到拉文塔森林里发现的一幅地图;我并不经常向人谈起它,因为它实在难以理解,并且我自己也将它视为一个秘密。这幅地图被镌刻在一块石板上,似乎是因为被保存在石质的地下室里,它没有像我们找到的其它石板那样经受岁月的无情侵蚀而模糊不清,上面能看见一些非常清晰尖锐,但是完全看不出在摹画什么的古怪线条。
最初我们一直在根据那些线条猜测这是一幅描绘怎样形象或场景的石版画,但是没有一个设想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直到有一天,我看着办公室墙上贴着的世界地图,突然脑子里打了个激灵。我拿着石板的照片同地图仔细比对,发现它一侧的线条与南美洲西岸的海岸线十分相似;而如果这样看,另一边的线条则准确地勾勒出了整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东岸,每一个细小的褶皱都同地图上几乎完全吻合。但是在这些描绘地图的曲折线条之间,有一条明显更为顺滑的曲线,绕过现今的巴拿马运河的位置,把大概在墨西哥湾的地方同石板的“最南端”连接了起来——但是那里同我们所知道的南极洲相去甚远,看上去像是两块靠得很近的陆地的一角。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我的同事们,但是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嘲笑我是异想天开:直到大航海时代人类才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壮举,三千年前奥尔梅克人怎么可能就绘出太平洋沿岸的准确地图了呢?我无法反驳他们,但是心里却也无论如何没办法把呈现在我眼前的东西当做仅仅是某种巧合。随着时间的流逝,连我自己也开始不禁怀疑,也许只是太想要在这个领域取得点什么惊世骇俗的成就的欲求使我产生了错觉和执念;打我小时候对玛雅人遗迹着迷的时候做梦也会梦到,就像约翰·斯蒂芬斯在奇琴伊察那样令人激动不已的伟大发现。
在我告诉他这件事之后,在他发来的下一封邮件里,有两幅严重泛黄的中世纪的心形地图照片。他在邮件中告诉我,这是他早先在纳高拍下的两件文物收藏品,一幅叫做“布雅舍”地图,还有一幅是“欧文斯·费内”地图。我马上注意到这些地图中不同寻常的地方:它们描绘出了在那一时代不可能具有,精确的全球地理——特别是在南极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块像是从中间被海沟分隔开的陆地——和我的石板上描绘的一模一样;而这,他告诉我,同地震波探测得到的南极冰盖下的地形完全一致。这些文物虽然落入私人收藏,但是它们在曾经展示过的博物馆中都留下了档案,甚至在大英百科全书中都能查到,绝无捏造的可能。
那之后我又陆续收到了几封邮件,内容是来自古代史诗的片段:
“在神民居住的梅鲁,太阳和月亮每天从左走到右,星星们也一样……梅鲁山峰光辉灿烂,战胜了夜晚的黑暗,使日夜难分……曙光乍现,到世纪太阳升起之间,好几天的岁月已经流过。日与夜相加,便成为神民的一年。”(《摩柯婆罗多》)
“亚利安纳乐土受到神明的诅咒,万物冰封,植物无法生长,白色掩盖了绿色,寒冷的死亡笼罩了大地……太阳、月亮和星星,一年只升起和落下一次,一年就好像一天。”(《伊朗亚利安纳史诗》)
“维达还有瓦利气喘吁吁
向南逃窜穿过火焰地狱
天候却陡变得怡人凉爽
蓝天纯净无暇闪烁奇光
……
光明神巴德尔重返人间
他和弟弟黑暗神霍德尔
不再仇杀化干戈为玉帛”(《埃达》)
我无法描述当我看到这些东西时的感觉,脑子里全是我的石板和地图,无法思考其它任何事情;那天下午和晚上我就像是着了魔一样不停地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网上搜寻有关的信息。隔天他又发来一封邮件,问我有没有兴趣同他一起去南极看看。我马上就应下了。
3月初,我来到乌斯怀亚——南美洲的最南端,最接近极圈的地方。我在港口见到了我那位朋友;不仅有他自己,还有他带来的一艘破冰船,以及一整支工程队的人员。
“我要这里建个研究所——”他向我指了指地图,那里是南极洲大陆的中间位置。“现在的地磁南极;它每年都在移动,所以我要打提前量,还要加快手脚。”
我并不理解地磁南极同我们的考古发现有什么关系;但是看起来这位朋友了解的比我多得多。潜意识里,我有一种可能会因为问些不该问的问题而惹他不快的隐忧。
“你知道吗?在过去的亿万年里,地磁极倒转过许多次,每一次都引来世界的异变。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六千年以前——”,他突然话锋一转:“其实前期工程已经完成了;像我之前告诉过你的,我们在那里有常温住所。这个计划我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我认识你以前就开始了。真想马上就给你看看;那是了不起的工程。”
“我以为我们不是应该往冰盖下面挖吗?”我还是忍不住问道。
“是的;没错。”他对我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微笑。“将我们的伟大国度从冰盖下解放出来。”
几天后,我们进入了极圈。我以为我们会先到哪个科考站作为落脚点再进一步深入,但是破冰船直接驶在浮冰的海域,顺着冰盖的裂隙向内深入。船身不断地因为接触到巨大冰块而发生震动,但是船上所有人都像是例行公事一般,没有表现对现状的丝毫担忧;我的朋友则好像有事在身,一直没在甲板上露面。我自己对于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也只好听天由命,告诉自己事情一定早已安排妥当并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按捺住心中的不安——尽管我并不清楚“计划”到底是什么。
3月中旬的时候,天空变得越来越昏暗,那几天船航行得也越来越慢——事实上感觉就是越来越艰难了,而我心中惴惴不安的感觉也随之越来越强烈——我从没听说过冰盖中有一条裂隙可以如此深入南极洲的腹地。但是有好几次,当我来到甲板上,看向天际时,所有的不安突然间烟消云散——我恍惚觉得自己离什么越来越近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怀念,内心沉醉于一种安详,平和而又温暖的感觉中。有好几次,船员从甲板上把我拉回舱室,埋怨我差点把自己的鼻子和手指冻掉——比那更严重的是肺冻伤,让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终于有一天,船驶进了一片稍微开阔的水域;这里就像是一个港湾,前面再没有路了。工程队和船员们登陆在冰面上,花了几个小时把各种像是打孔机一样的设备从船上卸下来。我穿上全封闭的防寒服,跟着其他人乘坐着柴油机和电动机驱动的各种载具在冰原上行进。我看见我的朋友坐在最前面的一辆小巧的四轮车里,带领着整个队伍。过了也许十几个小时,一个透明的穹顶出现在太阳方向的地平线上。我知道我们到了。
“欢迎来到天堂。”
当我进入那个透明温室的时候,他如此欢迎我。
从隔离间进入温室内部,我终于得以摘下总是布满雾气的保温头罩。突然之间,就像是从嘈杂的尘世进入了神秘的净土般,我发觉自己的脚步声响彻了整个空间,莫名地产生了一种像是做了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一样的羞愧感。这个偌大的空间里几乎什么也没有,由一个透明的穹顶罩了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泡;如果不是最顶端附近有少量的积雪,你甚至察觉不到这穹顶的存在。
“太阳。过去的五个月里一直在天空中盘旋着,让我们的温室得以维持现在的温度。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向它道别了。”
我看向他所指的方向。太阳正在沉沉落去,一半消失在了地平线以下。天空的色泽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层次感:靠近太阳落下的地平线处泛出一种珍珠般的温润的美丽色泽,然而随着视线向头顶上方延伸,神秘的蓝黑帷幕蔓延过了整个天际,上面点缀着闪烁的繁星和月亮,以及朝向太阳的方向被隐隐约约照亮的云朵。
“中国有句古话,‘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天堂。”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吗?”我问道,“其他人呢?”
“他们在底下。他们是我雇来干活的;但是你不一样。”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清醒了过来。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终于冲破了那层一直蒙在我脑海里的雾霭,使我陷入了对现状的难以置信,而后是巨大的恐慌之中。
我看着窗外一望无际的白色世界,捂住了脑袋;然后,像是触电了一样,猛地远离了我那位“朋友”的身边。
“你是我们伟大复兴开端的见证者。”他说。
那之后,我被“非正式”地囚禁在这个白色地狱中的庇护所和牢房里两个星期。我的“朋友”再也没有来看过我,只是他的几个手下每天都来给我提供食物和水。我无数次萌生从这里逃跑的念头;但是我心里也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比起被冻死在零下六十度的室外,我不得不选择等待未知命运的降临。
一天清晨我浑浑噩噩从地板上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身处彩色光芒之中。我就那么躺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那不是梦境的延续。
像由粉色到紫色渐变的,像帷幔一样的极光向两侧拉开了;在南极洲三月的太阳最后的余晖中,一个影子浮现在了天幕。起初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常有这样的幻觉,或是光影的巧合。但是这个人形的削瘦黑影没有任何要随着我的意识清醒而消散的迹象。就像是默默地昭告着自己的存在一样,它从地平线上耸立而起,从远方的天穹俯视大地;我能感觉那视线正看向我这里。我不由得向它伸出手去,想要揭开它披着微光的面纱,却发现我的手并不能从眼睛那里遮住它分毫;我突然意识到,我并不是用眼睛看到了它——我的头脑中有一个比视野更真实的领域,而它就矗立在那里。此时,就像是一阵风,或是一股水流,有什么进入到了我的意识里——如此真切,如此清晰,不可置疑的真理与伟大的智慧本身,无法用语言诉说,只是如同醍醐灌顶。
我最终彻底平静了下来。
当我的朋友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地磁南极无形的伟岸之柱周围挥舞着他们的触手时,大地发出了隐秘的战栗。我感受到了地壳之下铁磁体岩浆的涌动;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我获得了它们所崇拜的的神祗眷顾,成为代表这一代自视为地球主人的人类在世代交替的见证人;它的化身向我显圣,告诉我关于这个世界将要发生的变革。但我知道事情远不止于此。
在这一切都结束以后,我会向新世代的主角传达来自过去的火种,正乌巴拉图图向吉尔伽美什传递了这个世代的火种一样;然后我将一个人静静死去。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唏嘘的;在“它”看来,我们随时间流逝的生命如同凝固在琥珀里,纤毫毕现。
山东 威海 环翠区(总部)
QQ: 1390573279
V信:khxk2018


- 无数据